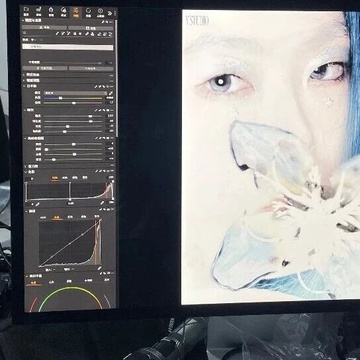渡洛西汀:渡一程,解千忧
2022/05/09
撰文:小琦
3月26日,渡洛西汀首张EP《沉溺于马里亚纳》正式发布。四个千禧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中的碎片感悟,简单的爱、炽热的爱、胆怯的爱、无意义的爱,变为旋律和故事,轻轻在心弦上撩拨。乐队成立两年,从0到1,从单曲到专辑,从校园比赛到第一轮巡演,被疫情偷走的大学生活,他们想抓住一切机会补回来。

大学城南站
广州大学城南站是一个换乘车站,地铁4号线和7号线汇聚于此,构成周围12所高校学生的主要出行方式。为了配合大学城的学术氛围,站厅里装饰了活字印刷版《弟子规》,可惜对面的广告灯箱经常破坏气氛,比如手游《原神》来投放的时候。
到达这一站前,地铁语音会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报站名,并提示“去往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的乘客,请准备”。这句话伴随大学城20万靓仔靓女走过四年,甚至更久的时光,和他们的记忆牢牢绑定在一起。
成员刚好来自这两所大学的乐队渡洛西汀,把这句到站提示录下来,放进第二首原创作品《等太阳落山,就一起做梦》里。歌曲开头唱道:“阳光打在十九点三十八分的公车上”,陈宏彬写下这句话时正好是某个周一的19:38,乐队又挑了一个周一的19:38把它发表。看似有什么深意,其实没有,不过是生活中琐碎的感受,琐碎之余也调一调情,“别说我爱你,我们一起做梦”。
渡洛西汀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在大学城众多学生群体中留下痕迹,或者更远大一点,在中国独立音乐的浪潮里,留下广州大学城的痕迹。

欢迎来到音乐协会!
从大学城南站D口出来,是鼓手酱油就读的华南理工大学。B口则指向主唱兼贝斯手陈宏彬和吉他手小明所在的广东工业大学,乐队另一位吉他手王子桢去年刚从这里毕业。
上大学前,四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接触过乐器:酱油从小学习打击乐,参加过乐团,中学时因学业中断;小明听过摇滚乐后爱上了电吉他音色,走野路子开始自学;陈宏彬初中成绩不好,爱玩电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干脆把电脑砸了,买了把木吉他;王子桢的音乐经历最丰富,从八九岁开始,钢琴、口琴、木吉他、电吉他轮番上阵,不曾间断。
他们加入了各自学校的音乐社团,华工吉他协会和广工大地音乐协会。这两个协会在广州高校间颇有名气,除了每年固定举办摇滚、重型音乐节,还穿插有大大小小的联合演出,稳定输出了许多高质量学生乐队。特别是大地音协,创立于1987年,成员数百人,前辈乐队如沼泽,新秀如Hyper Slash皆出自于此。
可以说没有这两个社团就没有渡洛西汀,三年下来,他们也以四个人百分之百的会长率作为回报。

大一新生小明在音协里认识了大三会长王子桢和大二准会长陈宏彬,会长认真负责,把他自学时的错误指法一一纠正。与此同时,酱油在华工吉协恢复练鼓不久,王子桢当时乐队的鼓手介绍她去商演,演出现场她认识了渡洛西汀初代贝斯手,后者又把陈宏彬和小明介绍给她。
以上人物关系没看懂就算了。总之,这场商演成为一切开始的契机,2019年圣诞节,渡洛西汀乐队正式成立。
乐队第一首歌《蒂芙尼蓝》像是在完成作业。“组乐队”这个课题已经建立,没有原创作品似乎说不过去。2020年4月,广州因疫情推迟返校,被困在家的陈宏彬决定迈出开题后第一步。谈起创作动机,他有些不好意思:“当时像是为了写歌而写歌,动机不够纯粹,急于把作品呈现出来,对整首歌也没什么特别明确的概念。”
他交出了一幅送给耳朵的蓝色拼贴画,蓝色的汽水、蓝色的大海,或许还有一条蓝裙子,清爽又浪漫。陈宏彬是福建人,故乡靠海,当他对歌曲创作这件事还不那么熟练的时候,潜意识选择了自己最熟悉、最有安全感的意象进行表达。
酱油和小明收到《蒂芙尼蓝》弹唱加鼓机的demo时,紧张又兴奋,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参与编曲,两人尽力把对乐器的理解融入其中。酱油很喜欢这种温柔含蓄的曲风,心想一定要把它编好。彼时王子桢还没正式加入,作为好朋友在一旁提提建议。刚开始大家有点不得章法,磕磕绊绊地也算顺利完成了。
该如何衡量一首歌的成功与否呢?商业数据?技术技巧?还是业界评价?对这些仍在念书的年轻音乐人而言,没有什么比从0到1的过程更值得喜悦。

歌里的故事,是也不是
乐队成立以来,成员们一边增进技艺,一边抓住机会参加各种比赛和演出。磨合的机会越多,矛盾暴露得越明显。半年后,初代贝斯手因理念不合而离队,2020年11月,王子桢加入,陈宏彬改弹贝斯,阵容固定至今。
转年9月,渡洛西汀开始为发行EP作准备。EP中的歌都是新写的,陈宏彬起头,大家一起完成,平均创作一首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五首新歌按顺序听下来,不难觉察出背后完整的故事线,从爱意萌发,变为相爱,经历断开和重拾,直到告别。看似写的是情歌,实则真真假假,充满年轻人独处时默默消化的小心思。
这些歌是陈宏彬主创的,有他的影子,却不是他的日记。他只搭建足以让故事继续的框架,而非为了把人框进去反复臆测。跟女友分手时他写下《星星也属于你》,复合后带来《回头是小狗》,调整时间线放入EP中,转眼构建出新的故事。那时还没流行起“小狗文学”,歌曲上线后人人争做小狗,关于一刀两断和破镜重圆的歌词,被披上忠诚与长久的外衣,拥有了更时髦的表述。
听起来像另一个故事,没关系,音乐每时每刻都在发酵新的故事。
他们喜欢在歌曲中加入人声采样,EP五首歌里占了三首,有时是几十秒的独白,有时是一问一答的对话,似乎这样做,可以离听众近一点。“希望能让人觉得是与自己有关,或者身边发生的事,音乐没有那么远,只不过我们几个用它呈现出来了,这些感受很多人都经历过。”
在《偷走海浪的婚纱》尾奏部分加入采样是小明的主意,如果像惯常一样使用器乐堆叠,叙事性不够完整。跟他们一起去录音的朋友,从旁观者的角度听这首歌,脑海中浮现出电影《苏州河》的画面,二者温柔却强劲的后劲儿有几分相似。于是,这个本该以浪漫终结的故事多了一个锋利的结尾,现实里没有马达,城市里也没有傻瓜。

新歌快录完的时候,乐队才取了专辑名。名字往往能先入为主,为欣赏氛围定下基调。《沉溺于马里亚纳》,他们希望把听众带入一种“沉溺”的状态里。“不是有那种心理测试嘛,看到马里亚纳这个地名,一类人会觉得是海沟,另一类人觉得是群岛,两种都可以。”陈宏彬说。
“不过马里亚纳海沟是世界最低点,沉溺在最低点比较符合我们几个人的性格,都挺闷的。”他补充道。
 《沉溺于马里亚纳》专辑封面
《沉溺于马里亚纳》专辑封面
渡一程,解千忧
Duloxetine(度洛西汀)俗称“千忧解”,是一种用于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以此作为乐队名,难免让人担心他们的精神状态。
其实他们只是比较内向,容易社恐,偶尔会因敏感陷入短暂的抑郁状态,远未达到需要诊断的程度。按现在的话说,应该是“更容易emo”。因为自身这样的性格特点,他们尝试去感受抑郁症患者的心情,去触摸那些躲在角落里的孤单群体,沉入情绪暗面进行创作,把“度”改成“渡”,希望作品能起到“渡一程”、“解千忧”的疗效。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渡洛西汀还是想试着通一通,最起码,不要嫌人家吵闹。
去年5月,乐队经历过一段3个月左右的“emo期”。那时刚发完单曲《等太阳落山,就一起做梦》,王子桢忙于毕业的各项事务,其他三人开始准备期末考试。毕业后,王子桢回到郑州老家,本想去去就回,结果遇上了“720”特大暴雨,返广之路遥遥无期。

灾害和疫情搅得人心惶惶,乐队成立以来,他们一直被写歌和演出推着往前走,突然停滞下来,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创作也失去了动力。王子桢加入到朋友的救援队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抢险转运工作。陈宏彬偶尔会打来电话,一聊就是两个小时,互相排解低落的情绪。
转机出现在8月,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联络,渡洛西汀终于敲定了经纪人AJ,并把作品版权交给街声,还认识了素有广东年轻乐队“助推人”之称的制作人伍绍维。乐迷熟悉的许多乐队,像是悶餅Hoo!,右侧合流等等,作品基本都出自他之手。相识后,伍老师也担任起渡洛西汀单曲和EP的制作工作。

渡洛西汀又恢复了动力,很快发表乐迷共鸣极强的第三首单曲《缺乏亲密关系能力》。这首歌由小明作词作曲,交给酱油来唱,描述当下年轻人中常见的“回避型依恋”问题——对亲密关系有所向往,又持消极态度。小明曾在纪录片中了解到“洛西极限”的概念:当行星和环绕它的卫星之间的距离小于此极限,潮汐力会导致卫星碎散。浪漫残酷亦如人类社会。
酱油为这首歌编出了一段相当复杂的鼓,复杂到其他人会担心她演出时能不能一边唱一边演奏的地步。数学系的酱油在编鼓的时候总忍不住用到排列组合,创造一些奇怪的、不那么整齐的节奏型,加上技巧变形,鼓的难度很大。
这也是渡洛西汀编曲上的特点。理工科出身的四人以三大件为基础,不怎么用到program,会花很多时间探索音符排列组合的可能性。用效果器调音色的时候,也不单从听感出发,而会考虑物理波形的样子。他们像生产产品一样,强迫症般地追求结构的严谨与逻辑。
所以才有了乐队简介中“理科浪漫”的形容。

严谨并不意味着冰冷的编曲机器,只是借助理科思维对抽象情绪进行描述,服务的终究是艺术与美。例如《马里亚纳清晨》里王子桢超过一分钟的吉他solo,最初是录制时即兴演奏的,他想象自己下沉到海沟最深处,用大音程做出深海的感觉,中段选最简单的音推起情绪,引出释放灵魂般快速的旋律。
这样大段的吉他solo,渡洛西汀在现场演出中安排了很多,让歌曲的叙事性更强,遐想空间更大,制造出不同于录音室版本的听感。
“夜晚的意义”
成立两年、发专辑、办巡演,按以前的标准,对学生乐队而言已经算是进展神速。可出生于千禧年前后,随快节奏文化一同长大的渡洛西汀似乎还觉得有点儿慢:“好像没有正式走出去,谈不上什么建树,今年EP也发了,是时候办一场巡演,给自己的乐队生涯留下一个里程碑。”

如今王子桢是郑州一名小学数学老师,利用周末和假期往返广州排练。异地不同的防疫政策为巡演徒增变数,演出变成了对心理承受能力的考验,弹完最后一个音符前,随时都可能被叫停。
即使这样,渡洛西汀还是要演。因为如果等下去,没人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