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音乐真是美术老师教的
2017/03/23
撰文:琉球、clouds
长久以来,在音乐人的队伍中,潜伏着一大批拥有美术背景的创作者。他们有的是美院的尖子生,有的出生美术世家,从小习画,有的已经成为人民教师,把美术传授给下一代……但不约而同的,他们都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了无限的为音乐事业的奋斗中。
好好的美术家不当,为啥要来做音乐?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三位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科班出身的模范生:鬼否乐队、杜昆与莫宝,看看在他们眼中,美术和音乐是如何互相交织、彼此影响的。
鬼否
新晋数学摇滚乐队。成立于2014年的杭州,全体成员来自中国美术学院,主唱丸易玄拥有个人设计品牌 maru,吉他手张一杨参与设计的“上下杯”被马云、王石等大佬收藏。目前已发行EP《神游大王》和《宇宙蛋》。

我们都是从小喜欢画画,高中的时候下决心考美院,于是比较正式地开始学画画。我们觉得美术跟音乐是不分家的,对于比较文艺的人来说,画画和组乐队是两大梦想,很多画画的都会去学乐器,只是有些人没坚持下来而已。所以大学以前,我们也都因为兴趣去学键盘、吉他、鼓等。进入美院后,我们纷纷加入学校的摇滚社,最终碰到了现在的成员。
其实美院玩摇滚乐的环境和周围其他学校差异不大,生态环境比较差,同学听流行歌曲、网络歌曲比较多。学校也没什么资源倾向我们,老师比较支持剧社、民间手艺考察等工艺社团,对摇滚社一般持不支持的态度,连场地都不太愿意给我们。吉他手刚到摇滚社的时候,社团是濒临倒闭的状态。如果就美院玩音乐这个小圈子来说,整体会稍微浪漫一点,大家都喜欢追求酷一点、比较冷门的歌。香料乐队的主唱陈陈陈曾拉赞助出资举办了好几届的刮刀音乐节,以实验先锋音乐为特色,伴随每年的优秀毕业生展,比较有艺术气息。
 (图片摄影@Hasong)
(图片摄影@Hasong)
无论美术还是音乐,其实创作的过程是类似的,要么形式为先,要么观点为先。作为一支全部由美术生组成的乐队,我们可以把音乐里的很多元素,转换成一些美术术语去解释,互相照样能听得懂,而且更便于理解,美术和音乐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相通性。但另一方面,两者需通过不一样的感官去感受它,美术集中在视觉,音乐则注重听觉,两者有着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差异。在表达一些想法时,我们会灵活运用这两种形式。
由于我们都是学美术的,有自己的审美,所以演出的时候比较懂得穿着搭配。乐队的专辑及周边的设计也不太需要再找别人帮忙,像鼓手做新EP《宇宙蛋》的视觉设计时,大家都会直接提意见。因为是美术生,也会有一些跨界合作,比如之前有一个服装品牌blueError 找主唱王易玄合作,设计鬼否系列衣服,她就会加入一些乐队的元素比如歌词、专辑纹样。
 EP《宇宙蛋》封面
EP《宇宙蛋》封面
很多人一直想探究鬼否的音乐和美术作品之间有没有暗在的联系或连接点,我们自认为是没有。我们写歌的时候,会忘记美术生这一层身份,单纯服从于听力的审美,觉得这个东西好听,就去做了。乐队成员有做服装、陶瓷、平面设计等等,专业不太一样,品味也不尽相同:主唱王易玄喜欢比较超现实的一些跨媒体视觉作品比如Ed Atkins,还有新兴的网络快餐艺术家比如Don Elektro;吉他手张一杨喜欢Arne Åse、Steve Heinemann、桑田卓郎、滨田庄司,这几位分别代表了几个时代的陶艺家,也同时表达了各个时期的思想状况;鼓手龚啸比较喜欢宋画,比如画家范宽,喜欢当代艺术中结合科技手段和声音的池田亮司,具有历史感视角的艺术家Brian Tolle等。所以我们在美术方面的创作思路都不太一样,更不用说从一种媒材跳到另外一种媒材,肯定是有巨大区别的。
我们也不认为音乐和美术之间会强烈地互相影响,他们是相对独立的两块。我们大部分成员学的都是设计,设计是需要符合市场,考虑生产成本和适合的人群,而做音乐只要我们自己喜欢就好,满足自己大于满足别人。我们把音乐之外的身份当做一种普通的职业,没有觉得学美术的做音乐和别人做音乐有什么不同。
杜昆
民谣音乐人,画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日本三潴画廊的签约艺术家,作品在北京、香港、釜山等多地参展;2012年发行专辑《清波街上空的幽灵》;他将音乐与画画合体,创作了《众神闹》系列——欧珈源、木玛等音乐人的建筑肖像。

画画是童子功,音乐是半路出家。上国美附中那会儿是2000年前后,全校只有我一个人玩独立音乐。后来到了央美,北京的摇滚乐氛围比杭州浓郁很多,学院里很多玩音乐的同学,民谣、金属、朋克、电子乐……
我觉得我生下来就是为了画画,但这不妨碍我创作音乐。就像iPhone 生下来就是一部手机,但它要做相机,要当播放器,甚至把自己当成一台电脑。人也一样,有多面性,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音乐和美术作为两种艺术形式,都是靠能否打动人而证明其价值,都是把无形的奇思妙想落实为具体作品的载体。有时把美术理论翻译过来,直接就适合于音乐,比如虚实处理、质感肌理、细节和整体的关系、情绪的隐藏和爆发、节奏和色调的关系……
然而表现形式上音乐更倾向于动态,绘画更倾向于静态,而且绘画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管好自己就OK,但音乐需要合作。各种乐手、制作、录音、混音、VJ、灯光……需要不同专业的人在一起合作。
画《众神闹》系列时基本上是画谁就听谁的音乐,这样会更好地理解他/她的气质,然后转化到油画里去。

 《众神闹》系列中的谢天笑(上)和左小诅咒(下)
《众神闹》系列中的谢天笑(上)和左小诅咒(下)
《清波街上空的幽灵》的专辑封面是我自己的画作,《好奇者之梦》是给一个朋友的手绘动画作品做的配乐,除此之外就没有特意单独为音乐作画,或者为绘画配乐,做不好会很傻。在艺术品面前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没法知道你画的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音乐,如果只是在感受上来互译,是多余的。
 专辑封面取自《十四万四千》的一部分
专辑封面取自《十四万四千》的一部分
用当代艺术的标准来看摇滚乐,摇滚乐就完全“阵亡”了,相反实验先锋类音乐才是这个时代最“摇滚”的东西,当代艺术也非常具有“摇滚精神”,因为它们的核心都是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探索更多可能性、实验更多方式方法、拓展人类想象力的边界。
我的工作室分上下两层,下面是画室,上面是音乐工作室,因为是公寓楼,不能声音太大,所以我所有的乐器都是经过耳机发声的,没有音箱。

平常上午做音乐,下午画画,晚上看书,自己有一套适合自己的作息安排。绘画为主,音乐为辅,就像主食和配菜、右手和左手,就像母语和外语、工作和休息,就像太阳和月亮、光和影、上和下。
在绘画上,达利和贝克辛斯基是我上学的时候的偶像,洛佩斯和池田学在技法上影响了我,后来我画建筑画风景,还借鉴过宋代画家李嵩、范宽的技法,近两年自己的想法改变很多,受邱志杰老师的书影响很大。
莫宝
莫虚有乐队主唱,画家。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作品在北京、比利时、洛杉矶等多地参展;将热爱的摇滚乐与水墨结合,创造“水墨摇滚”系列作品;目前已发行原创纯音乐专辑《境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

受父亲影响,我从小写书法,中国历来有“书画同源”这一说,很自然就选择了广西艺术学院的国画专业。受黄公望影响很深,反复临摹他的经典作品《富春山居图》,让我体悟到中国水墨画的精妙与博大。西方的艺术家有杜尚、博伊斯,我很喜欢他们的颠覆性的观念艺术,并且将这种观念用到自己的水墨或音乐创作里。
“水墨摇滚”的命名很早,在我本科三年级时就有了。有一次我在上练习课,边听着激烈的摇滚乐,跟着旋律和节奏,毛笔自然而然把音乐里的情绪描摹了出来,随后一大批摇滚题材的水墨画也应运而生。到北京后,在2005年曾接受过《通俗歌曲•摇滚》采访,并发表了我的几幅摇滚题材的水墨画,文章的标题就打着“水墨摇滚”,大概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

 (“水墨摇滚”系列作品)
(“水墨摇滚”系列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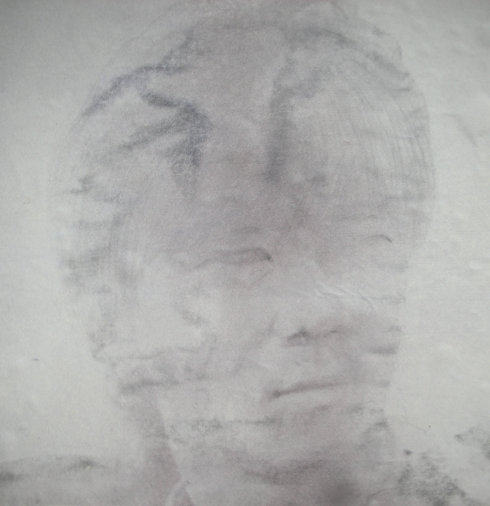 (“水墨摇滚”系列作品之崔健)
(“水墨摇滚”系列作品之崔健)
我在2004年本科毕业后就一直写歌,之后来到中央美院读研,为了参加学校吉他社摇滚之夜演出,就组了“莫虚有”乐队,成员都是吉他社的成员,还有就是隔壁宿舍的哥们儿。其实乐队处于初创阶段,还没怎么好好弄,大家就都毕业了。不同之处在于我是一个很蹩脚的主唱,排练起来很费劲。在央美我喜欢去听一些跨专业的课,比如去人文学院选修西川老师的文学课,去实验艺术系听课,搞行为艺术。
许多人都是音乐和绘画创作同时进行,虽然每个人所处背景与情境不一样,呈现出来的东西也很不一样,但我感觉内核应该是一致的。比如唐朝丁武的油画,除了具象写实外,的确是有史诗意味在里面。而窦唯的画,虽然也灵动朴素,但还是有人间烟火气息,和他这些年的音乐创作相比,音乐部分要飘渺仙逸得多。我自己的音乐大概比较像表现主义绘画吧!我的音乐有写实也有意象性。
如果有情感想要表达的我会选择音乐。绘画的功能在网络与多媒体时代已被削弱,画画于我而言,就是自我静修的一种方式。同时音乐也能调剂枯燥的绘画创作,画累画倦了,吼几嗓,写写歌,心情会愉悦很多。学美术的搞音乐,能营造出音乐的艺术性或者音乐的画面感,但也不够专一,音乐玩着玩着就玩别的去了。
“水墨蓝”系列作品是我这两年来的新尝试,很巧听到痛仰的《野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墨水的蓝颜色领我回家乡,觉得意境跟我的水墨作品很对路,算是巧合,不存在灵感来源,但我确实很喜欢这首歌。
 (“水墨蓝”系列)
(“水墨蓝”系列)
从西方古典音乐诸如巴赫、马勒、拉赫玛尼诺夫,到平克•弗洛伊德、莱昂纳德•科恩、汤姆•威茨,到国内的木马、左小祖咒、李志、小河都是我喜欢的。至于音乐对绘画的影响,有一首《六便士买你一幅画中不中?》,灵感来自梵高的一幅描绘麦田的风景画。绘画跟音乐一样,需要看原作,听现场,去感受那种扑面而来的冲击。
(本文图片来源:受访者、网络)
点击这里,进入杜昆的街声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