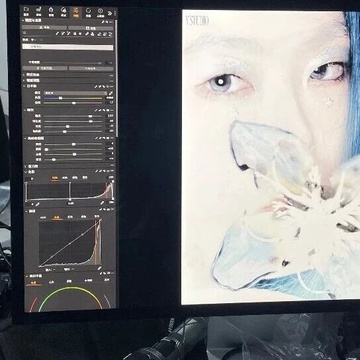野孩子:过去的远行是找寻意义,现在是春游
2017/11/11
撰文:孙大猴
街声独家专访
“过去的远行是找寻意义,现在是春游。”野孩子住在大理,张佺时常带着老婆孩子去云南乡下听民歌。问起和当年徒步旅行的差别,他半开玩笑说出了这句话。野孩子的歌成了一代又一代在外西北人的乡愁,2017年上海简单生活节大地舞台上,《黄河谣》响起,黄浦江边的世博公园,苍茫的西北景象就像夜幕一样落下来。
暮色低垂,暴晒一天后的兰州变得温柔而忧伤。天还擦着一点点亮光,三五成群光着膀子的老爷们,拎着几瓶黄河啤酒到黄河边上乘凉。走着走着,就那么十分钟内,月亮升起来,太阳落下去,一阵阵苍凉雄壮的歌声在岸边此起彼伏,其中夹杂着酒瓶子拿起后放在土地上的钝响,人们咀嚼的声音和小声谈话的声音。奔腾的水声夹在歌声里,头也不回向东流去。
这幅景象在张佺口中讲出来,纵然从没去过兰州,看着他的眼神,口音,无论身在何处,那种凝重和安稳都会像夜幕一样泼下来:“月亮照在铁桥上,我就对着黄河唱。”
远行吧,远行……
像日夜奔流的黄河水一样,张佺和小索沿着黄河几字弯一路北上。有时走上一天路都看不见人,但却能听见牧羊人的歌声在黄河边上盘旋,深深的河谷,目所能及,全被各式各样的歌声覆盖了。
张佺1968年出生在兰州,长在青海农村。记事儿开始,他就记得屋前屋后,都是“花儿”,这是流行于甘肃宁夏青海的一种民歌。上学经过田地里有人唱,年轻男女在天擦黑时对歌要唱,节日庆典,茶余饭后,漫山遍野都是“花儿”。
村民从家里去邻村串亲戚,没有其他的交通方式,只能走。路过山谷,独自行走的人都会唱上几句,听着自己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似乎半天的路程也没有那么难熬了。放羊的人,终日找不到人说话,也有放羊人自己的一套民歌。对于当地人来说,“花儿”“酒曲儿”这类民歌就如同成都人打麻将、喝茶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张佺后来回到兰州,“当年的兰州和西北的其他地方都差不多,除了车多一点,人多一点,气候地貌生活方式,都差不多。那些工地干活的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只能唱歌。”回忆起兰州的景象,张佺说。
现在的西北也经历着很大变革,手机里的网络歌曲席卷着大家。可民歌还在。前两年野孩子去青海,小公园里经常有人一起唱“花儿”,还拿着手机查歌词,一边翻着手机一边唱。只要这一辈人还在,这种音乐就不会消失。
 张佺在北戴河边的背影,张佺说,民歌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社交
张佺在北戴河边的背影,张佺说,民歌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社交
1980年代末,吉他风刮到了西北,但凡个青年,多少会弹点吉他,就算不会,家里也多半有一把。本来以民乐为主的走穴演出团体,也有很多变成了电声乐队。当时不到20岁的张佺听了不少打口带,“都是找封面看着比较狠的听”张佺说。于是张佺也学起了吉他,在乐队里成了一名贝斯手。
“当时成都比兰州的音乐环境要好很多,演出也多。我们想先去成都看看,下一站,下一站再去北京。”1990年,张佺去了成都,辗转杭州、广州等地,认识了小索。漂泊在他乡,两个人沿着黄河一路向北,徒步走过了黄土高原上的无数个村庄。
很多村庄虽然说是在黄河边上,但是黄河并没有给黄河边上的人们带来富裕和幸福。黄土高原上千沟万壑,眼见黄河水就在脚下,但是打水却要走十里八里山路。当时的张佺和小索背着琴,穿着打扮也不像当地人。“只要一进村子,十分钟以后就会有人过来找你。如果是邻村的人,他们都认识,不会大惊小怪。那样的村子里很少来外人。”张佺回忆道。
和村干部沟通沟通,说自己是音乐人,村里多半就能给他们安排住所、吃饭的地方,有时会让张佺和小索在村里人家轮流吃饭,住在村会议室。村里的人还会介绍一些当地爱唱歌的人给他们。当地不叫歌手,更不叫音乐人,叫“唱把式”。
 陕西省延长县的景象,河边的道路已经比当年张佺和小索走过的时候好了不少
陕西省延长县的景象,河边的道路已经比当年张佺和小索走过的时候好了不少
沿着黄河行走,有时候会听到放羊人遥远的歌声,路过延安东边的延长县附近时,黄河在脚下奔腾而过,天也下起雨,路只能经过一个人,如果对面有人,两个人都要侧着身才能过去。他们对这段路印象很深,因为心里一直想着:千万别掉下去。
在远行的路上,他们正好赶上甘肃省康乐县的莲花山花儿会,张佺和小索看着当地的民间艺人,用即兴的“野花儿”互相唱和,熙熙攘攘。听了不少西方音乐的他们又听见自己从小听到大的音乐,也好像变得熟悉又陌生。
“那时候到底是为了什么?两个人翻山越岭的,好像目的很明确,其实也不知道干嘛呢,还是希望找到和自己价值观相符的东西吧。”张佺说。
河酒吧
1996年3月,徒步旅行完成后,野孩子来到了北京。
当时演出原创音乐的地方不多,大多是在一些夜总会、歌舞厅临时做乐队的演出。1997年1月1日,野孩子在北京大西俱乐部进行了第一场演出,那场演出上张健吹口风琴,岳浩昆是贝司手,于伟民是鼓手。就这样,野孩子开始在北京的演出生活,乐手来回更换、磨合。
来自甘肃白银市的张玮玮和郭龙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1997年在兰州看过一次野孩子的现场,张佺和小索光头、一人一把琴,把张玮玮和郭龙震得不行,两个人看完演出没有车,生走了几十公里回家,一路上两个人还回味着演出:“好听!牛B!”颠来倒去说了一路。
多年后张玮玮回忆,听见野孩子的时候他一下子觉得生命又鲜活起来了,就像小时候听见监狱里放出来的、二十七八岁的老小伙儿们自由填词的囚歌一样,张玮玮在《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呢》里面这么描述囚歌:
唱之前要先说一段:“在监狱里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爹娘,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姑娘” ,然后齐声哼唱,“花开花又落”,一下把场景铺开了,这是起兴。然后,“直升飞机护送我,走进了大沙漠”——为什么是走进了大沙漠?西北最厉害的监狱是关白宝山的阿克苏重刑犯监狱,偷个钱包其实根本进不了,但是编词的人觉得进那样的监狱牛逼——“直升飞机护送我,走进了大沙漠,沙漠沙漠真寂寞,没有姑娘陪伴我,XXX思想哺育我,出去再作恶”。唱完了,大家再一起哼唱“花开花又落”,大场景一收,结束。
张佺在采访中也聊到了野孩子齐唱的形式:在其他音乐人的作品里,是很少出现齐唱的编配。
“齐唱是最原始的唱法,虽然流行音乐里比较少,但是宿舍唱歌,或者班里唱歌,大家都是齐唱,没有分声部的。”张佺说。野孩子的歌曲里通常是齐唱和合唱混合在一起。(齐唱是大家同唱一个声部,而合唱指多个声部一起演唱)《黄河谣》的录音里,前面都是以齐唱为主,在3分钟左右的段落里,分明分出了两个声部,“唱上一支黄河谣”也有两个声部。
 1990年代的张玮玮和郭龙在白银
1990年代的张玮玮和郭龙在白银
张玮玮1997年来到了北京。一到北京,他就联系了野孩子。野孩子住在地下室,穿得破破烂烂的,只要野孩子演出,他都会跟着去。2000年,他搬到小索家隔壁。
小索是出了名的豪爽,朋友们的脏衣服,经常都是攒够了就带到小索家,小索妻子开始做饭,大家喝酒唱歌,睡一觉,衣服晾干了卷走。一查暂住证,大家也是一窝蜂跑来小索家。
搬来没几天,小索过来问张玮玮会不会键盘,还给了他一张谱子,就是那首《死之舞》,让他拉着试试。他赶紧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叫他把白银家里的星海手风琴寄过来,没几天,张玮玮加入野孩子,担任手风琴手。
那一天,张玮玮第一次感觉到,白银的自卑、压抑、混乱和迷惘全被战胜了,“九十年代漫长的更新下载,完成了”,他到了人生的巅峰。(《那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呢》)
西北人喜欢抱团,张玮玮赶紧把形影不离的郭龙叫了过来。他们管张佺和小索叫“哥”,张佺和小索也有他们的“哥”。
 河酒吧门口的野孩子,后面那位外国姑娘笑得灿烂,也印证了河酒吧包容并蓄的内核
河酒吧门口的野孩子,后面那位外国姑娘笑得灿烂,也印证了河酒吧包容并蓄的内核
2001年,三里屯南街的一家酒吧转让,野孩子当时就盘算着给盘下来,自己能排练,晚上大家演出也能挣些钱。盘酒吧的钱不够,张佺小索联系到他们在兰州的“哥”,借钱。钱一到位,河酒吧开张营业。郭龙担任河酒吧第一任吧台。河酒吧不大,1.5m*2m的台子,三个人站着都挤,台下也就有个三、四桌。
野孩子起床就开始排练,排练完打扫卫生,下棋,酒吧开门,演出喝酒到凌晨三、四点。
那时候小河、万晓利都在天通苑买了房,两个人冬天骑摩托过来,在酒吧演完就喝,喝完摩托车往哪一扔,到谁家睡一觉,第二天再回去。在河酒吧演出是他们最喜欢的演出。IZ乐队马木尔、舌头、周云蓬、谢天笑、沙子乐队、赵老大,大家都在河酒吧演出过。
树村的摇滚青年、老外、记者、演员、什么样的人在河酒吧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李修贤、杜可峰、罗永浩这些名人也会来河酒吧,就像张佺说的:“河酒吧里有一个场景总会重复,到了后半夜,喝酒的喝得都差不多了,台上台下都唱着,或者即兴,房间里的所有人好像都认识,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河酒吧门口的野孩子
河酒吧门口的野孩子
那时候大家演完出就开始即兴,即兴的精彩甚至让大家怀疑平时排练的必要性。
2003年,非典来了,河酒吧倒闭,野孩子解散。2004年,小索因为胃癌去世。
这之后,张佺几经辗转去了云南定居。张玮玮跟着马木尔去了新疆,和郭龙一起辗转全国各地。
张佺弹起了冬不拉,一个人在各地演出。张玮玮和郭龙一起演出,发布了一张现场专辑《你等着我回来》。有几次在音乐节上见面,他们商量要不要一起演出。2010年,北京麻雀瓦舍,张佺和张玮玮郭龙做了“四季如歌”演出。
2011年10月31日,野孩子重组,参加西湖国际音乐节。
野孩子20年
在野孩子20年演唱会上,张佺弹吉他,张玮玮拉手风琴,郭龙和武锐演奏打击乐,马雪松弹吉他。细心的观众能听出来,现在的野孩子和二十年前录音里太不一样了。
之前录音中的野孩子,总是伴着电箱琴近乎急躁的扫弦声音,绵绵不绝,几个人的齐唱和合唱里透着无穷的劲头儿。这次,脍炙人口的《眼望着北方》从4/4变成了9/8拍,律动也不一样了。问起野孩子,他们笑了起来:“这个很简单,之前的4/4,唱着非常急,变成9/8,就多了一个八分音符,能多喘一口气。”
被视为代表作之一的《黄河谣》,也是一首复合拍子的歌曲。和很多数学摇滚乐队初衷不同,野孩子的复合拍子不是为了营造一种独特的风格,而只是唱出来就是如此。
在“花儿”“秦腔”等等地方民歌、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民歌乐曲里,拍子往往不像流行音乐这样单一,三拍子或者四拍子一直到底,大多会有一些复合拍子,对于听惯了民歌的人,听见拍子整齐划一的流行音乐,反而会有一种从彩色电视机变成黑白电视机的无聊和苍白。
所以,张佺走遍全国各地,和小索、现任低苦艾乐队的吉他手周旭东一起在杭州酒吧演出。演出之后,已经是半夜,白天熙熙攘攘的西湖也安静下来。张佺望着柔美的西湖,涌上心头的却是穿城而过、滚滚的黄河。月亮照在西子湖水里,柔美的月亮在张佺眼里也是黄河上庞大的、黑黢黢的黄河大桥。
 野孩子现在阵容,左起:张佺,张玮玮,马雪松,武锐,郭龙
野孩子现在阵容,左起:张佺,张玮玮,马雪松,武锐,郭龙
有人甚至会认为《黄河谣》是世代相传的民歌,是野孩子改编的结果。在民歌历史上,一首歌经过一代代民歌手的演绎,都会演绎出不同的版本,而这些版本优胜劣汰,留下来的往往是最禁得住考验的。野孩子曾经翻唱的《流浪汉》就是这样,很多人在新疆都听到过这首歌曲,于是就以为这是一首新疆民歌,其实这首歌却是从俄罗斯境内的吉普赛人发源过来的。民族的迁徙甚至战争,都会引起民歌的变化,有时候民歌手记不得本来的歌词,自己创作几句,也是很寻常的。
聊完了这些,张佺说:“不过《黄河谣》是写出来的,不是传下来的民歌,可能更多是因为用民歌的方式和手法吧。”
在野孩子的演出上,还有《死之舞》、《朋友再见》、《红河谷》这样的西方民歌,在野孩子的演绎之下,也显示出了独特的样貌。
野孩子现在住在云南大理,几个人下午一起排练,排练间隙,大家踢毽子。
张佺没事还是会到云南的乡下去探访民间音乐,说起现在的探访和之前徒步的区别,他笑了起来:“现在是带着老婆孩子春游去了!哄着孩子玩。”不过云南的很多民族没有语言,民歌讲的是民族的历史、传说,那个味道和西北的民歌大不相同。
野孩子在2017的上海简单生活节大地舞台上唱起了的新歌《不要拿走它》,张佺吉他的旋律中就能听出受到西南民间音乐的影响,带着花香鸟语的烂漫。
张玮玮说过他是没有乡愁的人,“故乡的工业城市只让我觉得羞耻, 野孩子的四五年才是乡愁”。各地的西北人,听见野孩子的歌声,都恍恍惚惚会在眼前出现故乡山川的样貌,这份乡愁甚至超越了年代,很多九零后零零后听了,也会泛上一种乡愁的味道,甚至创造出一种乡愁出来。对于西北人来说,无论眼前是什么景像,野孩子的歌声响起,都能看见奔涌的黄河水,月亮照在斑驳巨大的铁桥上。苍凉的歌声和波涛声一起,毫不回头向远方流走。